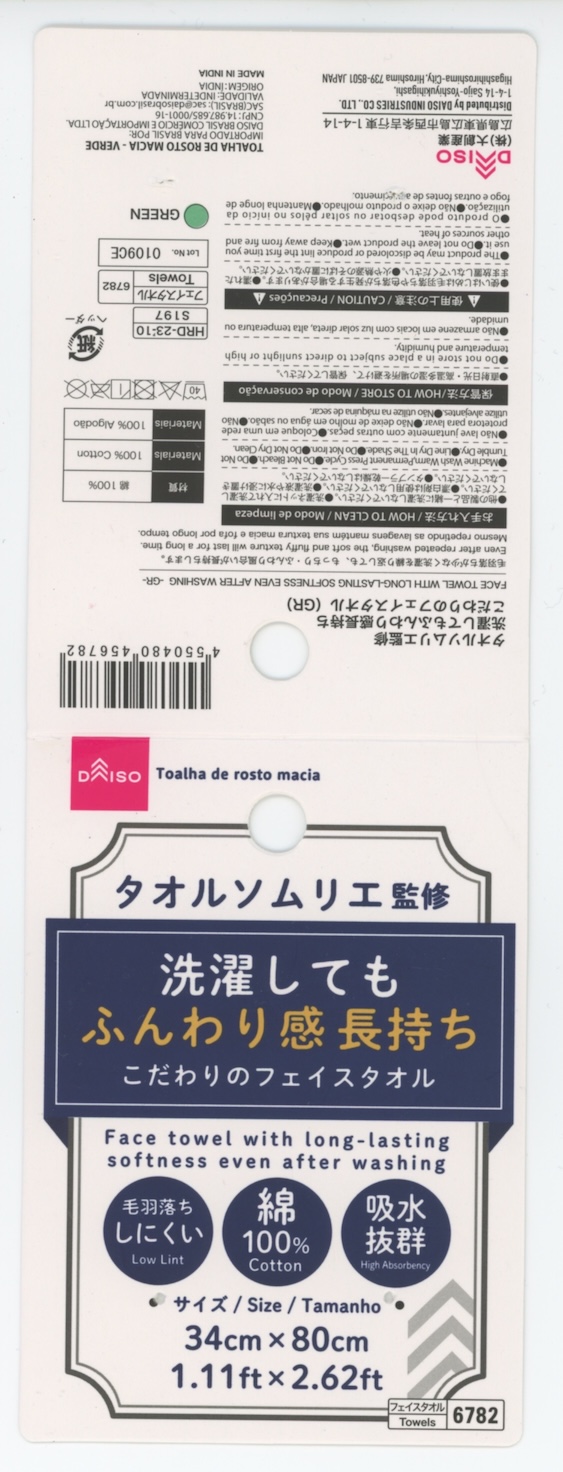这几天好像是 Google 发布了新的 AI 工具—— Gemini 2.0 Flash 。我不是 Google AI 的经常使用者,所以我就不清楚它到底哪个模型有什么特征,或是过去的两年里是怎么迭代至今的。不过今天看了几个网上的帖子和视频,似乎用过的人都对其能力表示惊讶。特别是我看介绍说它在生成图片方面有比较好的整合能力,以及可以通过用户所输入的文本提示,针对图片进行局部进行修改。
在一个网络视频中我看到了介绍者用 Gemini 2.0 Flash 做了一个菜谱,那么我就来仿造一下——生成一个图文并茂的奇幻世界的烹饪手册。
下面展示的就是实际生成的图片。需要说明的是,图片不是一次性生成的,我的生成步骤是:先要求 AI 用文字的方式输出菜单,然后再通过多次对话指示,为每个步骤生成一个配套的图片。
好的,这是一个分为六个步骤的奇幻世界幻想菜谱:
菜名:暮光森林的低语
食材基调: 夜光蘑菇、星尘香草、龙鳞坚果、月光泉水、影豹里脊肉(少量,可选)、梦 Wind 酿制的晨露蜂蜜。
第一步:收集与净化

食材: 新鲜的夜光蘑菇(3个,需带有微弱的蓝色光芒)、月光泉水(1小杯)。
烹饪手法: 将夜光蘑菇小心翼翼地用柔软的苔藓擦拭干净,去除表面的泥土和杂质。然后,将它们浸泡在月光泉水中,让其吸收月光的能量,并去除可能存在的微小毒素(奇幻世界的蘑菇特性)。浸泡时间约为一刻钟(奇幻世界的时间单位,约等于现代的十五分钟)。
第二步:唤醒香气
继续阅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