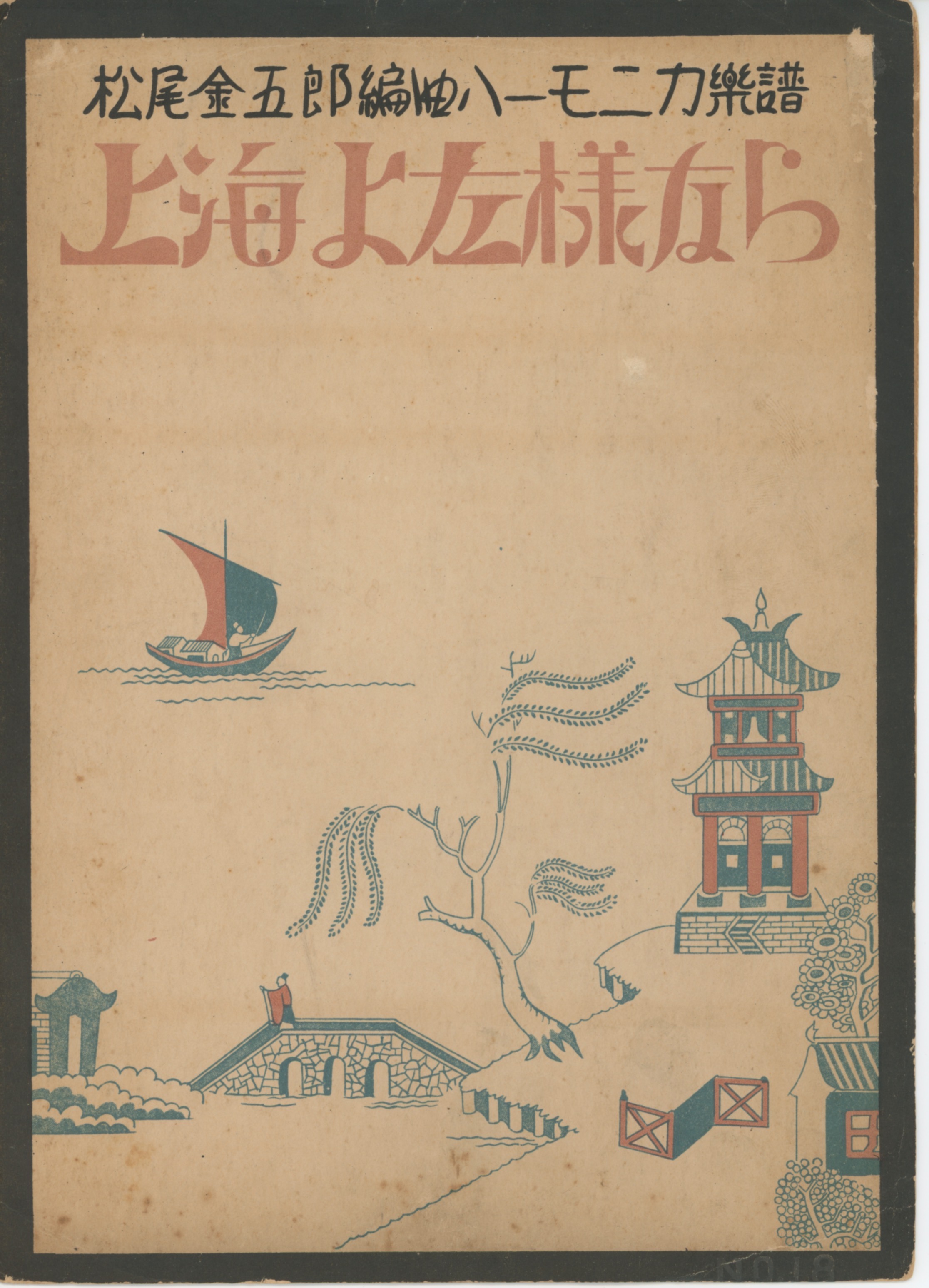昨天(2024年7月14日)好像是发生了一件对于美国历史,乃至可以说对于近未来的人类历史都多多少少具有影响的重大事件,也就是美国总统候选人Trump(特朗普/川普)遭遇枪击,并幸免于难的事件。
我的博客虽然不是紧追实时报道的,但对于这样一件历史事件——甚至于说还诞生了一张似乎可以载入教科书的照片的历史性瞬间——来说,在自己博客中记一记过去的这一天中发生了什么,或许对我个人来说还是挺有意义的。
其实昨天对我来说还是很平凡的一天,该看书看书,该去图书馆借还书也按部就班地进行了。因此就来简记一下吧。
昨天上午点亮手机屏幕后,看到大约2小时前的新闻(?)里播报了Trump遭遇枪击的画面,刷新数据流连看了几条发现都言之凿凿,且不乏有来自著名媒体的报道。于是我便到社交媒体上发言感叹:Trump真是命大呀。
午后,往返于图书馆的路上,去便利店看看报纸。不过因为都是日刊,应该是凌晨就排版印刷好并分发到各个卖点了,因此该事件就没有那么快等上纸媒。
空闲时间又在网上看了事件相关报道及分析,感慨Trump这位候选人、前总统确实真是命大,之前感染了2019年新冠病毒,康复出院;这次遭遇枪击,头一歪又避开了致命一击。
过了一夜,今天(7月15日)在便利店买了一份《京都新聞》,果然无论是这张报纸,还是日本其他全国性报纸,头版都是此事件了。我买的《京都新聞》中,首版、3面、10面和27面也是相关报道。此外,首版还报道了京都祇園祭,以及巴黎奥运会的倒计时(显示还有11天)。而在报纸的26面(社会2版面),还报道了京都宇治为在2019年夏天京都动画公司大楼遭纵火袭击案中失去生命的36人树立起雕像的新闻。而对于当年京都动画遭遇纵火一事,事件发生3天后的2019年7月22日,我也去献过花。
今天拿在手里的这张《京都新聞》,真实记录了我在日本期间,世界各地以及我所在地区各地的点点滴滴啊。